2025年11月02日·3 分钟
谷歌如何催生 GPT 却让 OpenAI 赢得人工智能竞赛
探讨谷歌如何发明了 GPT 背后的 Transformer 技术,却让 OpenAI 抢占生成式 AI 聚光灯;并分析这对创新者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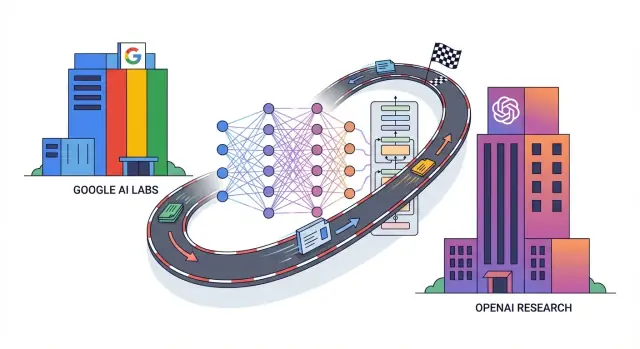
探讨谷歌如何发明了 GPT 背后的 Transformer 技术,却让 OpenAI 抢占生成式 AI 聚光灯;并分析这对创新者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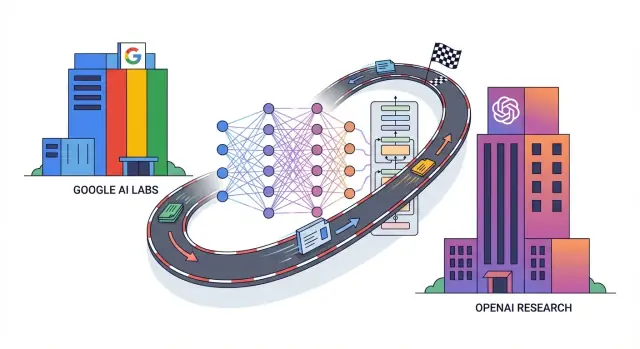
谷歌并非简单地“错过”了 AI,而是发明了让当前浪潮成为可能的一大部分技术——然后让别人把它变成了定义性的产品。
谷歌研究人员创造了 Transformer 架构,这是 GPT 模型背后的核心思想。那篇 2017 年的论文——“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展示了如何训练能以极高流利度理解和生成语言的超大模型。没有那项工作,我们今天所知的 GPT 很可能不存在。
OpenAI 的成就并非出自魔法般的新算法,而是一系列战略决策:把 Transformer 按远超多数人认为可行的规模放大,结合巨量训练运行,并把结果打包为易用的 API,最终推出 ChatGPT——一个让数亿人直观感受到 AI 的消费级产品。
本文关注的是这些选择和权衡,而非隐秘的戏剧或个人英雄与反派。它梳理了谷歌的研究文化与商业模式如何使其偏向 BERT 式模型和对搜索的增量改进,而 OpenAI 则押注于更危险的通用生成系统。
我们将逐步讲到:
如果你关心 AI 策略——研究如何转化为产品,产品如何转化为持久优势——这个故事证明了比拥有最好的论文更重要的东西:有最清晰的押注并有敢于交付的勇气。
谷歌进入现代机器学习时拥有两个巨大结构性优势:海量的数据和已被优化用于大规模分布式系统的工程文化。当这些机器被用于 AI 时,它迅速成为该领域的引力中心。
Google Brain 起始于 2011–2012 年左右的一个侧项目,由 Jeff Dean、Andrew Ng 和 Greg Corrado 领衔。团队专注于大规模深度学习,利用谷歌的数据中心训练对大多数大学而言难以企及的模型。
DeepMind 于 2014 年通过高调收购加入。Google Brain 更贴近产品与基础设施,而 DeepMind 则倾向于长期研究(强化学习、博弈与通用学习系统)。
两者合力为谷歌提供了无与伦比的 AI 发动机:一个植入生产堆栈、服务于产品的团队,另一个则攻关“登月”式研究。
若干公开里程碑巩固了谷歌的地位:
这些胜利让许多研究者认为:若想研究最雄心勃勃的 AI 问题,就去谷歌或 DeepMind。
谷歌聚集了非凡比例的世界级 AI 人才。图灵奖得主如 Geoffrey Hinton,以及 Jeff Dean、Ilya Sutskever(离开后加入 OpenAI 前)、Quoc Le、Oriol Vinyals、Demis Hassabis 和 David Silver 等资深人物在少数组织与大楼内共事。
这种人才密度创造了强大的反馈回路:
精英人才与重投入基础设施的结合,使谷歌成为前沿 AI 研究常常起源之地。
谷歌的 AI 文化偏向发表与平台构建,而不是打造打磨到极致的消费级 AI 产品。
在研究方面,常态是:
在工程方面,谷歌大量投向基础设施:
这些选择与谷歌的核心业务高度一致。更好的模型与工具直接提升了搜索相关性、广告定向与内容推荐。AI 被视为通用能力层,而非独立的产品类别。
结果是:一家在科学与底层架构上占据主导的公司,将 AI 深度整合到现有服务中,并通过有影响力的研究广播其进展——同时对将新型面向消费者的 AI 体验产品化持谨慎态度。
2017 年,一小队来自 Google Brain 与 Google Research 的研究者低调发表了一篇重塑整个领域的论文:“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作者包括 Ashish Vaswani、Noam Shazeer、Niki Parmar、Jakob Uszkoreit、Llion Jones、Aidan Gomez、Łukasz Kaiser 与 Illia Polosukhin。
核心思想看似简单却极具颠覆性:可以舍弃循环与卷积,仅用注意力(attention)构建序列模型。该架构被命名为Transformer。
在 Transformer 出现之前,最先进的语言系统基于 RNN 与 LSTM。它们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Transformer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位置信息通过**位置编码(positional encodings)**加入,使模型在无需循环的情况下知晓序列顺序。
由于所有操作都可并行且基于稠密矩阵乘法,Transformer 能清晰地随数据与算力扩展。这种可扩展性正是 GPT、Gemini 与其他前沿模型所依赖的。
相同的注意力机制也可以推广到图像 patch、音频帧、视频 token 等,使得该架构成为多模态模型(能读、看、听的统一骨干)的自然基础。
更关键的是,谷歌公开发表了论文,并通过后续工作与像 Tensor2Tensor 这样的库让该架构易于复现。全球的研究者与创业公司能够阅读细节、复制设计并将其放大。
OpenAI 正是这么做的。GPT‑1 在结构上是一个Transformer 解码器堆栈,采用语言建模目标。GPT 的直接技术祖先是谷歌的 Transformer:相同的自注意力块、相同的位置编码、相同的可扩展押注——只是应用在不同的产品与组织背景下。
当 OpenAI 推出 GPT 时,它并非从零发明新的范式,而是采纳了谷歌的 Transformer 蓝图,并把它推进到大多数研究团队不愿或无法达到的程度。
最初的 GPT(2018)本质上是一个用简单目标训练的 Transformer 解码器:在长文本上预测下一个 token。这一想法直接源自谷歌 2017 年的 Transformer,但谷歌当时更关注翻译等基准任务,而 OpenAI 把“尺度化的下一个词预测”视为通用文本生成器的基础。
GPT‑2(2019)将同一配方扩展到 15 亿参数并使用更大的网络语料。GPT‑3(2020)跃升到 1750 亿参数,在万亿级 token 上训练,使用大规模 GPU 群集。GPT‑4 延续这一模式:更多参数、更多数据、更精细的策划与更多算力,并辅以安全层与 RLHF,使其在对话中更有用且更可控。
在整个演进过程中,算法核心仍与谷歌的 Transformer 十分接近:自注意力块、位置编码与堆叠层。飞跃之处在于 sheer scale(纯粹的规模)与不懈的工程实现。
谷歌早期的语言模型(如 BERT)面向理解任务——分类、搜索排序、问答;OpenAI 则为开放式生成与对话进行优化。谷歌发表了许多最先进模型,然后进入下一个论文课题;OpenAI 把单一思路做成了产品管线。
来自谷歌、DeepMind 与学术界的开放研究直接滋养了 GPT:Transformer 变体、优化技巧、学习率日程、尺度定律和更好的分词。OpenAI 吸收这些公开成果,然后在专有训练运行与基础设施上大量投资。
知识火花(Transformers)来自谷歌。把这一思想作为公司级押注、发布 API 并推出面向消费者的聊天产品的是 OpenAI。
谷歌早期在深度学习上的商业成功来自让其核心赚钱机器——搜索与广告——更聪明。这个背景塑造了它如何评估像 Transformer 这样的新架构。与其竞相打造开放式文本生成器,谷歌更倾向于加倍下注能使排序、相关性与质量提升的模型,BERT 就是完美契合者。
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是一个仅编码器的模型,训练目标为掩码语言建模:句子的一部分被屏蔽,模型需在两侧上下文的帮助下推断被遮挡的 token。
这一训练目标几乎完美契合谷歌的问题:
更关键的是,编码器式模型能无缝嵌入谷歌已有的检索与排序堆栈。它们可作为成百上千个特征中的相关性信号,提升搜索而无需重写整个产品。
谷歌需要的是可靠、可追溯且能变现的答案:
BERT 在不破坏既有搜索界面或广告模型的前提下改进了这三点。相比之下,基于 GPT 的自回归生成对现有业务的直接价值不那么显而易见。
开放式生成引发了公司内部的尖锐关注:
能通过政策审查的大多数内部用例都是辅助且受限的:Gmail 自动补全、智能回复、翻译和排序提升。相比之下,编码器式模型更容易被约束、监控与证明合理性,而不是把一个可以回答健康或政治问题的对话系统大规模公开。
即便谷歌拥有可运行的聊天与生成原型,一个核心问题仍未解决:优秀的直接答案会否减少搜索查询与广告点击?
一次就给出完整答案的聊天体验会改变用户行为:
高层倾向把 AI 当作搜索的增强,而非替代。这意味着通过排名优化、丰富摘要与逐步的语义理解来部署 AI——正是 BERT 擅长的方向——而不是冒险推出一个独立又可能破坏商业模式的对话产品。
单个决策各自看起来理性:
总体上,它们导致谷歌在把 GPT 式自回归生成大规模产品化方面投入不足。研究团队确实探索了解码器式大模型与对话系统,但产品团队缺乏强烈的激励去发布一个:
而 OpenAI 没有需要保护的搜索王国,它相反押注:一个高度能干、公众可访的聊天界面——即便并不完美——会创造巨大的新需求。谷歌对 BERT 与搜索的聚焦延后了其面向消费者的生成式工具的进入,为 ChatGPT 率先定义这一品类留下了空间。
OpenAI 于 2015 年创立为非营利研究实验室,由数位科技创始人资助,他们既看到 AI 的机会也看到风险。最初几年它看起来类似 Google Brain 或 DeepMind:发表论文、开源代码、推动学术前沿。
到 2019 年,领导层意识到前沿模型将需要数十亿美元的算力与工程投入。纯非营利难以筹集这类资金。解决办法是结构性创新:OpenAI LP,即一个在非营利之下的“有上限盈利”公司。
投资人现在可以获得(有限上限的)回报,同时董事会保持对广泛有益 AGI 的任务关注。该结构使得签署大规模融资与云算力协议成为可能,而不至于完全变成传统创业公司。
许多实验室优化的是巧妙的架构或高度专业化的系统,而 OpenAI 做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押注:如果你持续增加数据、参数与算力,极其大型的通用语言模型可能会出乎意料地强大。
GPT‑1、GPT‑2 与 GPT‑3 遵循一个简单公式:大部分都是标准的 Transformer 架构,但更大、更长时间训练并用更多样的文本数据。它们不为每个任务单独定制模型,而是依靠“一个大模型,多种用途”的想法,通过 prompt 与微调实现多样化应用。
这不仅是研究立场,也是商业策略:如果一个 API 能支持从文案工具到编码助手的数千个用例,OpenAI 就能成为一个平台,而不仅仅是研究实验室。
2020 年推出的 GPT‑3 API 使该策略具体化。与其把大量软件放在本地或推出范围窄的企业产品,OpenAI 暴露了一个简单的云 API:
这种“API‑first”方法让初创公司与企业去负责 UX、合规与领域专业性,而 OpenAI 专注于训练更大模型与改进对齐。
API 也很早就创造了明确的收入引擎。OpenAI 不必等到完美的整品再出手,而是让生态系统去发现用例,并替它做产品研发。
OpenAI 一贯选择在模型尚不完美时就发布。GPT‑2 曾因安全顾虑采取分阶段发布;GPT‑3 通过受控内测进入世界,带着明显缺陷(幻觉、偏见、不一致性)。
这一理念最明显的体现是 2022 年末的 ChatGPT。它并不是 OpenAI 最先进的模型,也不算非常精细,但它提供了:
OpenAI 把公众当作巨大反馈引擎,而不是在私下无限调优模型。护栏、内容审查与 UX 随周而变,根据观察到的行为演进。
OpenAI 对规模的押注需要巨大的算力预算。与微软的合作在这点上至关重要。
从 2019 年开始并于随后几年加深,微软提供了:
对 OpenAI 来说,这解决了一个核心瓶颈:能在专用 AI 超级计算机上进行训练,而无需自建云或自筹全部资金。
对微软而言,这是差异化 Azure 并将 AI 快速注入 Office、GitHub、Windows 与 Bing 的方式。
所有这些选择——规模、API‑first、消费级聊天与微软交易——构成了自我强化的循环:
OpenAI 并非优化为发表完美论文或做谨慎的内部试点,而是为这个复合循环做优化。规模不仅仅是更大的模型,而是快速扩张用户、数据与现金流,以持续推动前沿。
当 OpenAI 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推出 ChatGPT,看起来像一次低调的研究预览:一个简单的聊天框、无遮挡的免费访问和一篇短博文。五天内用户超过一百万,数周内 Twitter、TikTok 与 LinkedIn 上到处都是截图与用例。人们用它写文章、调试代码、起草法律邮件、头脑风暴商业点子——仅靠一个工具就能做到许多事情。
该产品并不像“基于 Transformer 的大语言模型演示”;它就是:问任何问题,得到答案。这个清晰性使技术对非专业用户瞬间可读。
在谷歌内部,反应更像是警报而非赞许。公司宣布进入“code red”。Larry Page 与 Sergey Brin 被重新召回参与产品与战略讨论。长期致力于对话模型的团队突然受到强烈审视。
工程师们知道谷歌拥有大致可比的系统。LaMDA、PaLM 与早期的 Meena 已在内部基准上展示了流畅对话与推理能力。但这些系统被封存在受限工具与严格审核背后。
在外界看来,谷歌被突袭了。
在技术层面,ChatGPT 与谷歌的 LaMDA 是近亲:都是基于 Transformer 的大型语言模型并针对对话微调。差距主要来自产品决策,而非架构本身。
OpenAI:
谷歌:
在被迫展示应对之策时,谷歌于 2023 年 2 月公布了 Bard。这次预览试图模仿 ChatGPT 的对话魔力:向 Bard 提问,得到妙答。
但其中一个重点回答——关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发现——是错误的。该错误出现在谷歌自己的宣传材料中,几分钟内被发现,并在一天内抹去了数十亿美元的市值。这强化了一个严酷叙述:谷歌来得晚、犹豫且草率,而 OpenAI 显得自信且准备充分。
对谷歌员工而言,讽刺性极强。模型的幻觉与事实性错误是大语言模型的已知问题。差别在于 OpenAI 已经用清晰的 UI 提示、免责声明与“可试验”定位让用户接受这些问题,而谷歌却以完美发布的包装对外,错误暴露时代价更大。
ChatGPT 相较谷歌内部系统的优势,既不是因为更大的模型,也不是更新颖的算法,而是执行速度与体验清晰度。
OpenAI:
谷歌动作更慢,优化为“零差错”,并以光鲜的发布包装 Bard,而非把它当作学习阶段。到 Bard 推向用户时,ChatGPT 已成为学生、知识工作者与开发者的日常习惯。
谷歌内部的震惊不仅来自 OpenAI 的好模型,而是一个更小的组织把谷歌帮助发明的想法打包成了大众喜爱的产品,并在数周内重塑了公众对谁领导 AI 的看法。
谷歌与 OpenAI 起点有相似的技术基础,但组织现实极为不同,这种差异决定了围绕 GPT 式系统的几乎所有决策。
谷歌的核心业务是搜索和广告,这一引擎产生稳定而可观的现金流,大部分高层激励与保护它相关联。
推出一个强大的对话模型可能会:
因此默认策略是谨慎。对于 OpenAI 而言,没有现金牛,其激励更接近生存:上线有价值的模型、赢得开发者注意、签下大算力协议,把研究尽快变现。
谷歌经历过反垄断审查、隐私争议与全球监管,这段历史形成了一种文化:
OpenAI 接受强模型在公开场景下会显得混乱这一事实。公司更强调在护栏下迭代而非长期封闭完善。两者都谨慎,但产品风险容忍度相差甚远。
在谷歌,大型上线通常需通过多重委员会、跨组织签核与复杂 OKR 协商。这会拖慢横跨 Search、Ads、Cloud 与 Android 的任何产品进度。
OpenAI 的决策集中在小范围领导层与聚焦产品团队。关于 ChatGPT、定价与 API 的决定可以迅速做出,再根据真实使用调整。
多年来,谷歌凭借发表最好论文与训练最强模型占优。但当他人能复现这些研究时,优势转向研究加上:产品设计、开发者体验、数据反馈回路与上市速度。
OpenAI 把模型当作产品基底:发布 API、发布聊天界面、从用户处学习,然后把反馈用于下一代模型。
谷歌则多年把最强系统作为内部工具或有限演示封存。等到尝试规模化产品化时,OpenAI 已经建立了习惯、期望与围绕 GPT 的生态。
差距不是谁更懂 Transformer,而是谁有意愿且结构上能把这种理解迅速转化为面向数亿人的产品。
在技术层面,谷歌始终是强国。它在基础设施方面领先:定制 TPU、先进的数据中心网络与内部工具,使得训练超大模型在数年前就变得常态化。
谷歌研究推动了模型架构(Transformer、注意力变体、专家混合、检索增强模型)、尺度定律与训练效率的前沿。许多定义现代大规模 ML 的关键论文来自谷歌或 DeepMind。
但大量创新停留在论文、内部平台与在 Search、Ads 与 Workspace 中的狭义功能里。用户看到的更多是若干小而分散的改进,而不是一个统一的“AI 产品”。
OpenAI 走了不同的路。技术上它构建在他人已发表的思想上(包含谷歌的工作)。它的优势在于把这些思想打包为清晰的产品线:
这种统一的包装把原始模型能力变成用户能立刻采用的东西。谷歌以多品牌、多表面发布强模型,而 OpenAI 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名称与流程上。
一旦 ChatGPT 成功,OpenAI 获得了谷歌曾经占有的心智默认地位。开发者优先在 OpenAI 上试验,写教程、基于其 API 构建产品、向投资人推介“基于 GPT 的创业点子”。
底层模型质量的差距(如果有的话)比不上分发差距重要。谷歌在基础设施与研究上的技术优势并没有自动转化为市场领导地位。
教训是:赢得科学不足以万无一失。没有清晰的产品、定价、故事与整合路径,即便最强的研究引擎也会被专注的产品公司超越。
当 ChatGPT 暴露出谷歌在产品执行上的滞后,公司触发了公开的“code red”。随之而来的是加速、有时混乱但确实认真的 AI 战略重整。
谷歌的第一步回应是 Bard,一个基于 LaMDA(随后升级到 PaLM 2)的聊天界面。Bard 既显得匆忙又谨慎:访问受限、推送慢、产品约束明显。
真正的重置出现在 Gemini:
这一转变把谷歌从“试验聊天机器人的搜索公司”重新定位为“以 AI 为先的平臺与旗舰模型系列”,尽管这一定位落后于 OpenAI 的先发优势。
谷歌的优势在于分发,因此重整聚焦于把 Gemini 嵌入用户已有习惯所在:
策略是:若 OpenAI 赢得了“新鲜感”与品牌,谷歌仍能凭借默认存在与与日常工作流的深度整合来取胜。
在扩大访问时,谷歌强调其 AI 原则与安全姿态:
权衡是:更强的护栏与更慢的试验速度,对比 OpenAI 更快的迭代但偶有公开失误。
在纯模型质量上,Gemini Advanced 与顶级 Gemini 模型在许多基准与开发者反馈中与 GPT‑4 竞争性相当。在某些多模态与编码任务中,Gemini 甚至领先;在其他任务上,GPT‑4(及其继任者)仍然设定基准。
谷歌仍落后的,是心智占有率与生态:
谷歌可以以其庞大的分发(Search、Android、Chrome、Workspace)为杠杆,把 Gemini 转化为令人愉悦的 AI 原生体验,从而缩小或逆转感知差距。
重整发生在一个不再只是谷歌对 OpenAI 的领域:
谷歌虽晚但认真地重置,意味着它不再“错过”生成式 AI 的时刻。但未来更可能是多极化:没有单一赢家,也没有某家公司能完全控制模型或产品创新方向。
对建设者而言,这意味着要设计策略,假定会有若干强劲提供者、强大的开源模型与持续的竞相超越——而不是把全部赌注押在单一 AI 堆栈或品牌上。
谷歌证明了:你可以发明突破却输掉第一波价值。对于建设者来说,关键不是为这种悖论感到惊叹,而是避免重演它。
把每个重大研究成果当作一个产品假设,而非终点。
如果值得发表,就值得为客户做原型。
人们倾向于做被奖励的事。
Transformer 是一种新的计算原语。谷歌主要把它当内部基础设施升级,而 OpenAI 把它当产品发动机。
当你遇到类似深刻的想法时:
品牌与安全顾虑合理,但以此为由无限期拖延并不可取。
构建分级风险模型:
不要等待确定性,而要设计受控暴露:渐进放量、强日志记录、快速回退路径、红队测试与公开沟通。
谷歌通过开源思想与工具启发了他人构建 GPT 式系统,然后在许多方面旁观别人把标志性体验做出来。
当你暴露强大能力时:
不能依赖某位高管或某个英雄团队的个人努力。
把转化过程嵌入公司运作:
谷歌最大的失误不是没预见到 AI,而是低估了自家发明在消费者手中会演化为何种样子。
对创始人、产品经理与高管的实用心态是:
未来的突破——无论在模型、交互界面还是全新计算原语——都会被那些愿意迅速把“我们发现了这个”转变为“我们负责把它交付”的团队商品化的组织所拥有。
谷歌的教训不是少发表或隐藏研究,而是要把世界级发现与同样雄心勃勃的产品所有权、明确激励与公开学习倾向配对。能做到这一点的组织将拥有下一波,而不仅仅是写出开启这一波的论文。
不完全是。 但谷歌确实发明了让 GPT 成为可能的核心技术。
因此,谷歌奠定了大量知识和基础设施。OpenAI 则把这些基础变成了第一波商业价值(ChatGPT 与 API)。
谷歌偏向于研究、基础设施和对搜索的渐进式改进,而 OpenAI 更专注于推出大胆的通用产品。
主要差异:
BERT 和 GPT 都基于 Transformer,但针对的是不同任务:
因为生成式模型会自由输出内容,谷歌认为它带来了风险且难以直接变现。
主要顾虑:
OpenAI 在三方面做了不同的重大押注,并持续执行:
将规模化作为战略而不是实验
把标准 Transformer 推向极限(数据、参数、算力),基于 scaling laws 而不是频繁更换架构。
API‑first 平台策略
早早把模型以简单的云 API 形式暴露出来,让成千上万的开发者发现使用场景并在其之上构建业务。
不是主要在能力上落后,而是在产品和叙事上被超越。
这种做法把“谁引领 AI” 的公众印象从“谷歌领先”转变为“ChatGPT/OpenAI 定义了 AI”。谷歌真正的失算,是低估了自家发明放到简单用户界面后能产生的影响。
ChatGPT 的优势更多来自执行与定位,而不是独有的新算法。
关键要素:
谷歌的 Bard 则显得:
对大多数构建者而言,这个故事强调了如何把深度技术转化为持久优势:
任何规模的公司都有可能犯“谷歌的错误”——把研究当终点而不是产品起点,或让风险规避流程阻止受控上线。
避免方法:
你不需要像谷歌那样大才能被卡住;只要组织结构与恐惧感超过了好奇与速度,就会出问题。
谷歌仍然是技术强国,并通过 Gemini 做出了积极的策略重置:
谷歌仍然落后的方面:
从技术上看,谷歌并不落后;但在面向公众感知和采用的产品化上,组织与决策使其行动更慢。
BERT(谷歌):
GPT(OpenAI):
简言之,谷歌优化的是让搜索更智能;OpenAI 优化的是让人们可以直接与通用语言引擎对话。
鉴于公司的规模和监管暴露,谷歌更倾向于把 AI 作为增强现有产品的工具,而不是早早推出可能颠覆其核心业务的独立聊天机器人。
以消费级聊天为旗舰产品
ChatGPT 把 AI 变得易懂:‘问任何事,得到答案’。它没有等到完美才上线,而是上线后从用户处快速学习并迭代。
这些决定形成了“用户→数据→收入→更大模型→更好产品”的正反馈循环,推动其超越了谷歌那种更分散、节奏较慢的产品化路径。
核心教训:有技术而无产品所有权是脆弱的。 如果你不迅速把想法变成用户熟悉的产物,别人会把你的创见变成定义市场的产品。
更可能的未来是多极化:若干强有力的封闭提供者(谷歌、OpenAI 等)加上快速发展的开源模型。谷歌并未“输掉 AI”,而是错过了第一波生成式浪潮后及时转向。竞争现已围绕执行速度、生态深度与与工作流的整合展开。